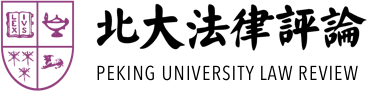“秋后算账”一文,唤起了对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的反思,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构成了反思的原点,针对溯及既往的问题,法庭给出的理由之一是纽伦堡审判创制的先例。因此,继续这场反思有必要回溯到纽伦堡审判本身。
1945年8月,美英苏法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和《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纽伦堡审判奠定国际法基础,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纳入其中。不过,这并没有让这场具有为法律与道义进行圣战色彩的审判幸免于管辖权拷问,相反,辩护意见开门见山地指责其将未事先明定的行为犯罪化并予以刑事追诉。[1]
溯及既往禁止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之一,犯罪除非在事前为法律明定,不得予以追究。事前未被明定为犯罪之行为,在行为时就没有不法性,事后的法律变动不能变更这一先在状态;法律不能要求国民在无法预料未来情形时谨小慎微乃至无所作为,毕竟,谁能保证不作为未来不会成为一项新罪行?
纽伦堡法庭针对禁止溯及既往的辩护意见给出了三点反驳:其一,1935年《德国刑法典》废除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规定;其二,禁止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不构成对主权的限制;其三,《勃利亚—凯洛格协定》等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中包含着禁止侵略战争的内容。拉德布鲁赫一改战前强调法的安定性甚于正义性的主张,强调人权超越法律和法律的合正义性,以此论证审判的合理性。不过,真正强有力的理由是,法庭自认无权对作为其建构依据的两份国际法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法庭以实证法主义基调肯定其管辖权,同时,又以一种自然法面向认定犯罪,形成自然法与实证法交融的政策性选择适用现象。
纽伦堡审判中为什么出现了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政策性交融?拉德布鲁赫转型构建的跨越之“桥”(考夫曼语)固然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却并不构成跨越动因;对敌人的复仇和对正义的追求才是真正的跨越动因。归根结底,纽伦堡是战争的无烟继续,而不是刑事审判;是政治活动,而不是司法行为。法国学者Mireille Delmas Marty将前南国际法庭的审判比作类似台球游戏原则的“正义的表演”,少数被告仅仅是直接行动对象,真正的目标则是赢得众多的西方听众。在此,审判显然是一种政治宣示,而不是纯粹的司法正义追求。
学者在研究暴力与屠杀规制时强调“对人性的否定”这一概念,指出:“受害者的巨大数量暗示了在苦难之外,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去人格化,即否认被杀者原本与刽子手一样,都被赋予着‘人性’的品质。”(Mireille Delmas Marty:“暴力与屠杀:刑法上的‘敌人’还是刑法上的‘不人道’”,余履雪译。)基于对“去人格化”的反对,任何有良知的公民都不会反对将刽子手“绳之以法”,朴素报偿与复仇意识的原初正义观念支配下的国民不难接受最终裁判,甚至可以高喊“这是正义的胜利”!正如Chateaubriand针对拿破仑屠杀雅法囚犯所评论的那样:“瘟疫从天而降,这是上苍在惩罚对人类权利的冒犯。”
不过,或许如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所指出的那样,纽伦堡审判是胜者的正义而非正义的胜利,这种对比定性反映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抗:胜者的正义更多体现的是战胜国代表的受害者发出的实质正义要求,正义性奠基于行为人先在的自然意义上的“恶行”以及这种恶性反映出来的“危险的敌人”特征,在此,“铲除危险的敌人最终排挤掉了对犯罪者的惩罚的观念”;正义的胜利则表征着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呼吁,强调对国民自由的保障与尊重以及由此而对恶行的不得已纵容,如果其没有在事前被宣告为犯罪的话。
纽伦堡审判是一场法治国家的非法治正义追求,实现了必须要实现的正义。不过,正义所借用的法律外衣难以掩盖审判的政治性,人们并不真正应用法律推理推进和保障这场审判,而是运用处理敌我关系的政治学思维推进这场“运动”,战犯们恐怕从未想过自己会被无罪开释,他们深知自己不是被告人,而只是“敌人”。
实质理性的冲动战胜了形式理性的理念,形式的法治国在此被迫让步于对敌人的惩罚了。值得思考的是,当形式的法治国让步于针对敌人的惩罚时,法治国还存在么?刑事法治难道不是蜕变为针对敌人的保卫战或还击战了?基于安全的紧迫需要和实质正义内心冲动而取消传统刑法中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混同了“罪”与“危险性”的概念,表征为刑事法律政策中的“极权模式”,任由其发展则可能使得刑法消弭于战争逻辑之中,铲除危险的敌人最终会排挤掉对犯罪者的惩罚。(Mireille Delmas Marty:“暴力与屠杀:刑法上的‘敌人’还是刑法上的‘不人道’”。)
敌人模式和不人道模式构成了暴力与屠杀犯罪性论证的两大类型,前者暗藏着一种刑法的军事化风险,可能使得不人道行动因为反恐战争等名义而畅行无阻。纵便人们能够保证一生不为非作歹,又岂能保证永远远离被无辜界定为敌人的厄运?一旦被赋予划定敌人进而剥夺或限制其实体与程序权利的权力,国家就彻底沦为力大无穷的利维坦,任何人都不能指望怪兽不发作而吞灭自己,既然链条已经被我们亲手砸断。
1985年,德国学者雅各布斯首次提出了“敌人刑法”概念,并不断完善。他指出,若要将抽象的法治国完全不加限制地实践,那么,这种完美的法治国会给恐怖分子提供好的机会,使他们变得活跃起来。敌人刑法,力图在犯罪人中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即普通的市民犯罪人和敌人,并针对后者剥夺更多的实体与程序权利。刑事处罚的前置化、不因前置化而相应地减轻法定刑刑度、从一般的刑事立法转变为防治型立法以及对于嫌疑人刑事诉讼上之保障较少构成了敌人刑法的基本特征。(Miguel Polaino-Orts:“以功能性破除概念迷思:敌人刑法”,徐育安译。)瓦勒特指出:“对特别危险的情况采用特别的斗争方式,这种作法可以在立法者的敌人刑法般的言说那里得到印证,这符合法治国的原则,同时,它是功能性和实践性的。”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甚至据此发展出了风险刑法的概念。如果说风险社会的技术风险特征使得风险刑法在根基上就难以证立的话,敌人刑法则更加集中地反映出对安全的需要,因而似乎可以得到正当化。然而,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于,谁来判断敌人?谁来主持对敌人的认定程序?谁又能保证自己不被误认为敌人?当人们设定越来越多的条件来限定这些非正常的处置时,作为公民的人们不必担心后果,但真的不必担心自己会被误认为丧失了那项被称为“公民”“朋友”或者“同志”“人民”的前提么?!
雅各布斯将根本性地偏离基本规范者称为“敌人”,他指出:“根本性的偏离者,对于具有人格之人所应为之行为不给予保证,因此,他不能被当作一个市民予以对待,他是必须被征讨的敌人。这场战争乃是为了市民的正当权利,即对于安全的权利而战,与刑罚有所不同,遭到制裁之人并无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敌人被排除。”(雅各布斯:“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徐育安译。)可是,将严重经济犯罪都纳入其中的如此扩张的敌人概念,或许能够满足安全保障需要,但是否严重过头了?如果经济犯罪人都属于敌人,那么,随时可能被敌人化而战战兢兢的国民就几乎没有自由可言!阿德特·辛恩面对法治国之凋零现状,忧心忡忡地指出,鉴于尖锐化的危险局势,刑法基本原则已有松动,法治国有转化为安全国(Sicherheitstaat)的危险。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曾经与我们缔结社会契约的国民,为什么能够被踢出社会之外而沦为非人格体?!在贝卡利亚看来,公民为了“平安无忧地享受剩下来的那份自由”而缔结社会契约,将最小部分的自由让渡给国家形成刑罚权,这最小部分自由以维护必要的安全为限,死刑尚不能从中衍生,勿论将某个人作为非人格体予以开除。康德认为,刑罚是对人自由意志本身的尊重,因此,在社群解散之时也必须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犯罪人是由于自己的先在行为而引致处罚,国家恰是由于将其作为目的才必须对其适用刑罚。
雅各布斯教授宣称从卢梭和康德中找到了敌人刑法的根基,可是,将一个人作为非人格体对待的行为无疑是将人彻头彻尾地工具化,这绝非康德所赞同而是其誓死反对的。在任何时刻,人,作为上帝的作品,都必须被作为人本身而予对待,即便是敌人;但是,在敌人刑法观念下,敌人却成为非人格体,沦为了类似入侵地球的外来生物一般的存在。在启蒙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民权刑法视野下,敌人刑法观念引致的强烈批判,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必然的。
如上的论述并不是指敌人刑法宣扬一种恣意的无时间限制的刑罚,相反,从现有汉语文献来看,尚未发现敌人刑法反对溯及既往原则。因此,即便在敌人刑法的理念下,纽伦堡审判的程序正当性也有待商榷。不过,纽伦堡审判及其后的艾希曼审判中,的确洋溢着敌人刑法的“敌人思维”。弗莱彻教授对敌人刑法的评论,正好可以借用来描述此类溯及既往的刑事追诉:“针对处死累犯或对其任意的徒刑的情况,最好的描述方法是,它们并不代表着实践正义,它们是对‘敌人’的战争行为。”如前所述,溯及既往的纽伦堡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实质理性驱动下的“对敌战争”,市民刑法的形式理性要求被淹没在对实质理性的追求之中。[2]
我国学者指出:“敌人刑法意欲成为与社会危险人物作斗争的刑法,没想到自己却首先沦为一个危险的刑法理念。”(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敌人刑法固然是一个危险的理念,不过,敌人刑法背后的敌人思维是法治视野下更加危险的东西,正是敌人思维本身时不时地将实质理性吁求带向了对“犯罪人”的战争,纽伦堡审判无疑就是如此的一场报偿之战,只不过,法庭上的战争没有硝烟弥漫和鲜血横流。我们宣称是由于战犯们的去人格化而将其送上法庭,但是,我们却在用敌人思维的方式把将他人去人格化的他们去人格化!
(袁国何,《北大法律评论》编辑。)
[1]《勃利亚—凯洛格协定》中可以觅得禁止侵略战争的芳踪,禁止危害和平的犯罪行为则可以在《哈格协定》与《日内瓦协定》中找到影子。不过,直到《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三类行为才在真正意义上被作为犯罪予以规定和正式对待!
[2]不过,阿伦特指出:“不是德国对正义的渴望,而是被受害者的‘报偿’和‘报复’欲望影响的世界舆论,才是他们的当事人目前麻烦的真正原因。”(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