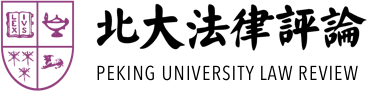2014年5月,著名演员黄海波因“嫖娼门”事件被行政拘留15日后,又被收容教育6个月。名人效应以及2013年劳教制度的废除等诸多因素使得该事件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在黄海波事件之初,最大的疑问(及误解)莫过于:劳教制度不是已经被废止了吗?为何还在适用?因为收容教育制度与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质上存在一致性:未经司法正当程序而长时间限制他人人生自由。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针对对象的不同,收容教育只是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劳动教养针对的对象更为广泛。而因为两者的实质一致性,诸多学者在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建议书(江平、应松年等40余位法学家、学者、律师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孙志刚事件让收容遣送制度寿终正寝,唐慧案、任建宇案也成为了压倒劳教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黄海波事件似乎为大家,尤其是广大非官方的法律工作者提供了彻底废止实质性的劳教制度、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又一次契机。然而,笔者并不认为黄海波事件是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有力支点。
首先,收容教育制度与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在表现形态上有所区别。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劳动制度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在公布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批准,以决议的形式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然而,这并未改变《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作为行政法规的性质和地位。以上两种制度的存在依据仅仅是行政法规。而构成收容教育制度的依据是《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其中前一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后一个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从这一点上看,收容教育制度有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双重依据。当然,这个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存在抵触《宪法》以及作为基本法律的《立法法》原则、精神以及具体条文规定的情形:《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而《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也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因此,简单的说收容教育制度违法,不够严谨。这实际上是法律与宪法、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相冲突的问题,而不是行政法规违反法律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缺乏违宪审查机制以及法律冲突解决机制,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更为艰难。
其次,对于卖淫嫖娼在制度上禁绝和严厉制裁是中国的一项公共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闭妓院、对于妓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摧毁娼妓制度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成就”、“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来加以确认的,也是作为与几千年来旧中国社会恶习相割裂的标志之一。1949年初,毛泽东明确指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而娼妓制度就是作为戕害、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之一。随后,自1949年11月开始至1958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或是采取暴风骤雨式的果断措施,或是采取逐步取缔的方式,最终在全国范围禁绝娼妓现象。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专门针对一项 “恶习”——卖淫嫖娼行为而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今年的“东莞事件”以及随处可见的相关街头广告告诉我们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只是暂时的、具有阶段性特征,但要求官方明确宣布放松对卖淫嫖娼现象管制,显然不大可能。然而,现在要求废止专门针对卖淫嫖娼行为而设置的收容教育制度,虽然并未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裁措施,它所传递的信号与中国历史上以及目前在该事项上的社会政策、官方的立场无疑是相悖的。因为,处罚措施的减轻往往是告诉大家这个领域的管制放松了。当法律规定遭遇公共政策,如何在博弈中进行协调是可以选择的路径,单纯的废止或抛弃一方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近十多年来,中国法治进步的基本路径多是:一个重大事件引起体制外各种力量的强烈反应,进而推动体制内力量的积极行动来废止相应制度。就以上所列情形来看,体制内目前的动力是严重不足的,甚至于是存在重大障碍的,尤其是在当前政府加大“扫黄打非”力度的情况下。体制外意见与体制内实践的严重冲突将无法促成收容教育制度废止的实践。因此,笔者认为黄海波事件对于收容教育制度的废止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当然,我们乐见许多地方正主动停用或少用《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许多法律的品位有待按照《宪法》的要求而进一步提高,中国立法体系的规范性也并未因为一部《立法法》而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仍未能在中国法制现实中植根。因此,有权部门如何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及法律冲突解决机制是中国法治这盘棋的“急所”,否则类似的事件还会层出不穷。具体到收容教育制度而言,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不可能做大的改易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规范收容教育制度的适用,将其纳入法制的轨道。例如,有限度地将多次卖淫嫖娼或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人员纳入刑法中的管制、拘役的制裁范围以最终替代目前的非法治化的惩罚方式。
(作者为高大应,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参与北大法学院沈岿教授、车浩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四位老师研讨后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