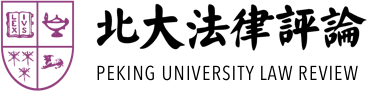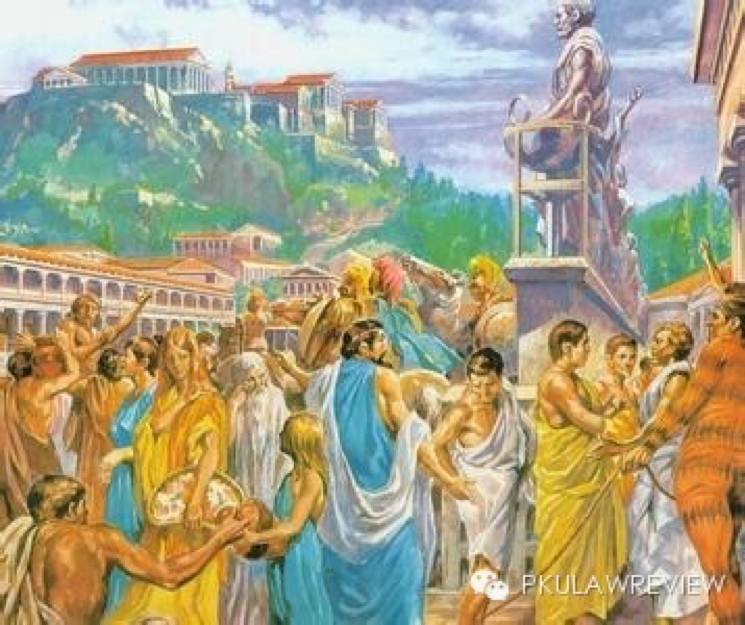
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经通过《爱丽丝穿精奇幻记》里矮胖子所说的话,指出民主常被“不加区别的用来用去……每个人都能随意指称任何统治是民主的,甚至连专制统治也可以说成是民主的”(达尔:《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的确,语词的含义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取决于使用者的主观界定。使用者不同,语词的所指也往往不同。所以,尽管大家都在使用“民主”一词,但由于界定不同而又未加以区分,也就难免产生沟通障碍。实践中,围绕民主问题的诸多政治执拗也大多是源于对民主的理解差异。比如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所引发的“真普选”和“假普选”之争之所以迟迟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和香港反对派对于民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别。鉴于此,将具有复杂面相的民主抽茧剥丝,梳理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脉络出来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正是在这一方面的初步尝试。
从逻辑上看,民主概念的分歧首先体现在民主是否仅仅指称一种政府形式的问题上。传统观念将民主单纯地理解为人民主权这一政治原则。不过,在托克维尔眼中,用社会方面的身份平等来定义民主才能真正说明民主社会和欧洲历史上其他社会的区别的根源所在。民主不只是传统观念中的一种政府形式,更是体现为社会关系与家庭中的身份平等。从这一定义出发,他将雅典的民主和欧洲的旧制度放在一起,把它们作为贵族政体的不同种类,认为这些“传统上被认为存在着本质差异的政体不过只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而已”(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当然,民主概念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撇开托克维尔的民主观念不说,单单是在那些从政府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传统观念中,民主含义也千差万别。一种是根据政府权威的起源(“民意”)或政府所服务之目的(“公共善”)来界定民主。另一种则是程序性的定义,将民主描写为一种组建政府的程序安排,主要为熊彼特所开创。1942年,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民主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做出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通过竞争人民手中的选票,个体获得做出决定的权力”(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经过近三十年的学术论争,熊彼特一派所主张的程序性定义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即使是在这一路径上,民主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最简单的定义是选举意义上的民主。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民主还包含着选举标准之外的其他广泛含义,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公民自由、政治的诚信和开放、知情及理性的协商、平等的参与等。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达尔的民主标准理论,他提出民主过程的标准包括:“有效的参与(effective participation)、选票的平等(equality in voting)、充分知情权(gaining 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对议程的最终控制(exercising final control over the agenda),成年人的公民权(inclusion of adults)”(达尔:《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由此可见,民主的含义可以通过上述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而在每个层次上,民主也都存在着丰富复杂的理解。层层看下去,如果将选举意义上的民主作为最基本的定义,那么每一层都在这一基本定义之外存在更具实质性的理解,对民主提出更高的界定标准。在这些实质性的理解中,民主不仅意味着选举民主,还对选举程序之外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之外的政治权威来源和政府目的以及政治之外的社会状况提出了要求。从这一角度看,民主的复杂定义大体可以清晰地简化为两大类:一类是选举意义的民主,民主是广大范围内的选民自由、公开、公平的投票选举过程;另一类则是实质意义的民主,民主不只体现为选举,还要处理好与公民自由、法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把握这一分析脉络,有助于更恰当的运用民主这一语词,并准确的理解别人口中的民主内涵。
(袁阳阳,《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