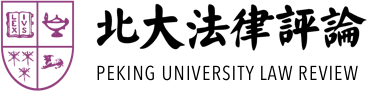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即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关键经济部门,以向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奥巴马在此处使用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作为美国总统一种行政权履行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比较法研究中,亦鲜有作者将这种文件形式作为讨论对象。不过,在美国人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行政命令司空见惯。许多重要的政策问题并未以立法的形式,而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2013年1月16日,奥巴马总统曾签署附有23个条款的控枪行政命令,绕过国会对枪支的使用进行限制。此举被称为是近20年来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控枪方案。同年5月9日,奥巴马再次就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新增政府数据都向公众开放,并支持计算机可识别的查询方式。由上可见,行政命令乃是美国总统贯彻其法定权力的重要手段,且涉及的内容可能会给普通公众带来显著影响。那么,究竟何为行政命令?美国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来源何处?行政命令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运作中发挥何种功能?
简单说,行政命令是由美国总统作为联邦最高行政首长对联邦所属各机构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指示。因此,行政命令本质上属于政府内部文件,并不直接针对公民。不过,效力范围的内部性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已经不适宜作为该文件影响公民权利义务时的抗辩理由,所以行政命令作为具有普遍影响力之文件的可能性不应受到过多的怀疑。总统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间接影响私主体的权利义务,比如奥巴马2013年初签署的关于规范关键基础设施部门计算机安全标准的行政命令即可对相关行业的运营商产生重要影响。
行政命令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明确,一般认为,其宪法基础是有关总统行政权的第2条:该条第1款授予总统以行政权,第3款要求总统确保法律被忠实地执行。虽然仅从模糊的宪法条文中推导出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有些牵强,但这显然并没有影响行政命令在现实中的巨大力量。它几乎具有与法律同等的地位,同时却不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程序。鉴于行政命令所具有的这项好处,它时常被各任总统用来规避碍手碍脚的国会,直接实现自己的意图。比如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为绕开由共和党掌握的国会,在两届任期内共发布364项行政命令,其中包括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其继任者布什总统略逊一筹,两任共签署291项;而奥巴马在已经完成的上一个任期内发出了144项行政命令。历史最高纪录保持者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他任内有记录的行政命令达到3700余项之多。不过,作为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赢得二战并连任四届的总统,这一惊人的数字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处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不可能等待慢腾腾的国会来完成所有重大决策。
行政命令在使用上某种程度的任意性令美国法学界担心它会造成专制总统的出现。因为这种形式的文件使总统可以在缺乏国会同意的情形下做出重大决定,甚至制定法律,而这与宪政主义以及法治的逻辑严重背离,并且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分权原则。所以,在大多数坚持传统法治主义的学者看来,通过国会和法院对总统进行制约十分必要。若国会反对总统行政命令的内容,它可以用相反内容的法律取消该项命令(假如总统对立法行使否决权,国会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假如法院认为总统行政命令内容不符合法律或者超越其职权范围,其同样有权将该命令撤销。然而现实中,这两种方法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威胁。首先,国会推翻总统行政命令需要三分之二绝对多数,这在一般国会表决中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国会对于总统的行政命令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其次,法院在面对行政命令时更是是保持谨慎尊重的态度,自美国建国至今,备案可查的行政命令已有13000余个,其中被法院撤销的仅有2个。
所以,尽管在理论上仍然遮遮掩掩,但是若就现实情形观察,行政命令已经毫无疑问地在事实上成为美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中原因并不复杂:面对繁重的社会管理事务,国会没有充分的精力制定事无巨细的规范,只能将具体处理问题、制定政策的权力交给行政部门;同样,法院缺乏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不当的行政命令提出挑战,只能对行政保持谦抑的态度。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行政命令的繁荣。在美国一般公众和媒体眼中,行政命令几乎与法律没有区别;对于法律人共同体而言,它们是处在阴影之中的法源。
不过,繁荣的背后也确实存在行政专制的危险。意大利学者乔吉奥·阿加本特别批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由西方民主国家做出的行政命令或政令的应用的泛化,宣称这种朝向“永久性的非常状态”的宪法的趋向。令人遗憾的是,行政国家的普遍出现已然使得这种趋向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变成了现实,传统的宪政结构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行政程序主义的兴起被视为是对这一挑战最为有力的回应,通过过程控制来保障结果的正义,从而修补在某种程度上受损的宪政结构。只是这一回应在目前离最后的成功尚有距离。如何处理行政命令以及其他不属于传统法源的行政规范的地位已然成为行政法学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俞祺 《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辑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